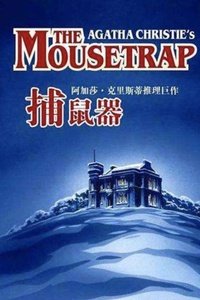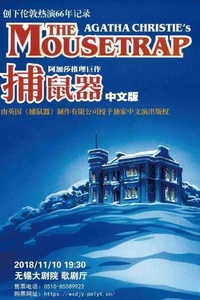给她一瓶毒药,她就能导演出一场完美的犯罪
“毒药有着特殊的魅力。”——阿加莎·克里斯蒂在《借镜杀人》中这样写道。

在阿加莎的职业生涯中,她用笔杀死了数以百计的角色。其中一些是淹死的,一些是被刺死的,一些人是被铁锹打死的,但是克里斯蒂最钟爱的方法,还是用毒,而不是采取暴力。
毒药能够顺利地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,让任何出场角色都能成为被怀疑的对象。在许多时候,毒药本身就是一个角色。
阿加莎曾经亲口承认,她对弹道学一无所知,不过却对毒药了如指掌,这或许就是她嗜好用毒的原因。
下毒者是冷峻而理性的,和用刀刺、扼杀的方法杀人的匪徒之间有着鲜明的对立。
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,阿加莎的小说中,她大幅度引入了心理证据,将心理学分析作为推理的一个重要手段。

如果说福尔摩斯们注重的是现场调查,擅长从指纹、毒药、血迹、烟灰等细微的痕迹中寻找破案的线索。那么,克里斯蒂笔下的侦探们最擅长的就是通过对话探究心理,找出罪犯。
正如她笔下最有名的侦探波洛所宣称的:“没有什么比隐瞒谈话更危险。说话……是人类用来阻止思考的发明。而它同时又是找出别人企图隐瞒什么的最可靠的工具。”
阿加莎让波洛和嫌疑人谈话,谈话的内容不但涉及案情,还有关于性格、喜好、牌技、服装等多方面,看似平实无奇甚至漫无边际的谈话中暗藏玄机。在冗长琐碎和看似随意的日常交谈中,波洛已经嗅到了凶手邪恶恐惧的气息。
通过对谈话的思考,波洛甚至可以揭露“合作谋杀”。在侦探小说里,一般都是一到两个嫌疑人是真正的凶手,这一模式在侦探小说里已经被创作者和读者所接受。但是在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中,车上的乘客证词中的谎言却一个接一个地被揭穿。最终证实这是一起由12个人共同参与的谋杀。

正如一位研究阿加莎的作家所说,“如果阿加莎让任何人物显露出一丝心理活动,那么谜底就不难揭晓了”,不过这样一来她所设置的猜谜游戏就会丧失令人爱不释手的吸引力。
比起柯南·道尔等以短篇小说见长,注重表现侦探个人智力的作家,阿加莎的推理更成熟、也更有魅力。
侦探小说大都有一个套路,一件惨案发生了,侦探到现场做一些无人能懂的勘查,接下来做一些神出鬼没的调查工作,更或者为找线索干脆消失几天,之后真相大白,揭开一个惊人的秘密。总之,为了能让结局足够出人意料,之前不管是案情还是侦探的调查那是能多匪夷所思就多匪夷所思。
不过读阿加莎的作品就完全不同了。你不必花费心思去猜测侦探做了怎样的调查,作者会把侦探的每一步调查以及他所获得的证据都摆在读者面前,让读者和侦探一同去破案。
她喜欢采用层层深入的手法设置悬念——并不急于通过一两次推理便求得实质性结论,而是留下更多空间给读者分析与想象。
“意料之外,情理之中”这个看似简单的衡量标准是古典解谜推理的最高境界,更是区分一、二、三流侦探小说作家的试金石。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第一部侦探小说《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》即展现了她不俗的创作才华。在一次神秘的案件中,凶杀案发生后,英格利桑先生受到了民众和警方的一致怀疑。然而,这个嫌疑人却有着可靠的不在场证据。经过审讯,被陪审团宣判无罪。结尾处,情节峰回路转。经过一系列调查,英格利桑先生确为杀人犯,只不过他用极为巧妙的方法掩盖了自己的罪行而已。
这是克里斯蒂侦探小说的处女作,但其独特的创作理念却初露端倪。巧妙运用读者心理,反其道而行之,开始就揭露凶手,而读者根据侦探小说的思维惯性,反而会将其排除在外,因此在揭示谜底时也就格外出乎意料。
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,阿加莎是人类史上最畅销的作家,总销量突破20亿本,豪不愧于“推理女王”的称号。
她一生写过66本长篇推理小说,14本短篇小说集。并以玛丽·维斯马科特为笔名写过6本其它形式的小说。

单论在法国,她的销量几乎是排名第二的法国文豪左拉的两倍。而按照译本种类和传播范围而言,其在世界的辐射范围仅次于《圣经》和莎士比亚的著作,迄今为止至少被翻译成103种语言。
她的话剧《捕鼠器》自1952年11月上演以来,直到如今还在继续,已超过2万5千场,保持着伦敦戏剧公演最长的记录。
今年秋天,这部推理巨作再次被搬上了舞台。


打开《捕鼠器》(The Mousetrap)前,关于故事本身,能够泄露的“天机”是:封闭的空间,开放的时间,暧昧错杂的身份;欲盖弥彰的眼神,看不见血腥,听得见心跳。

【演出详情】
上海场:
无锡场: